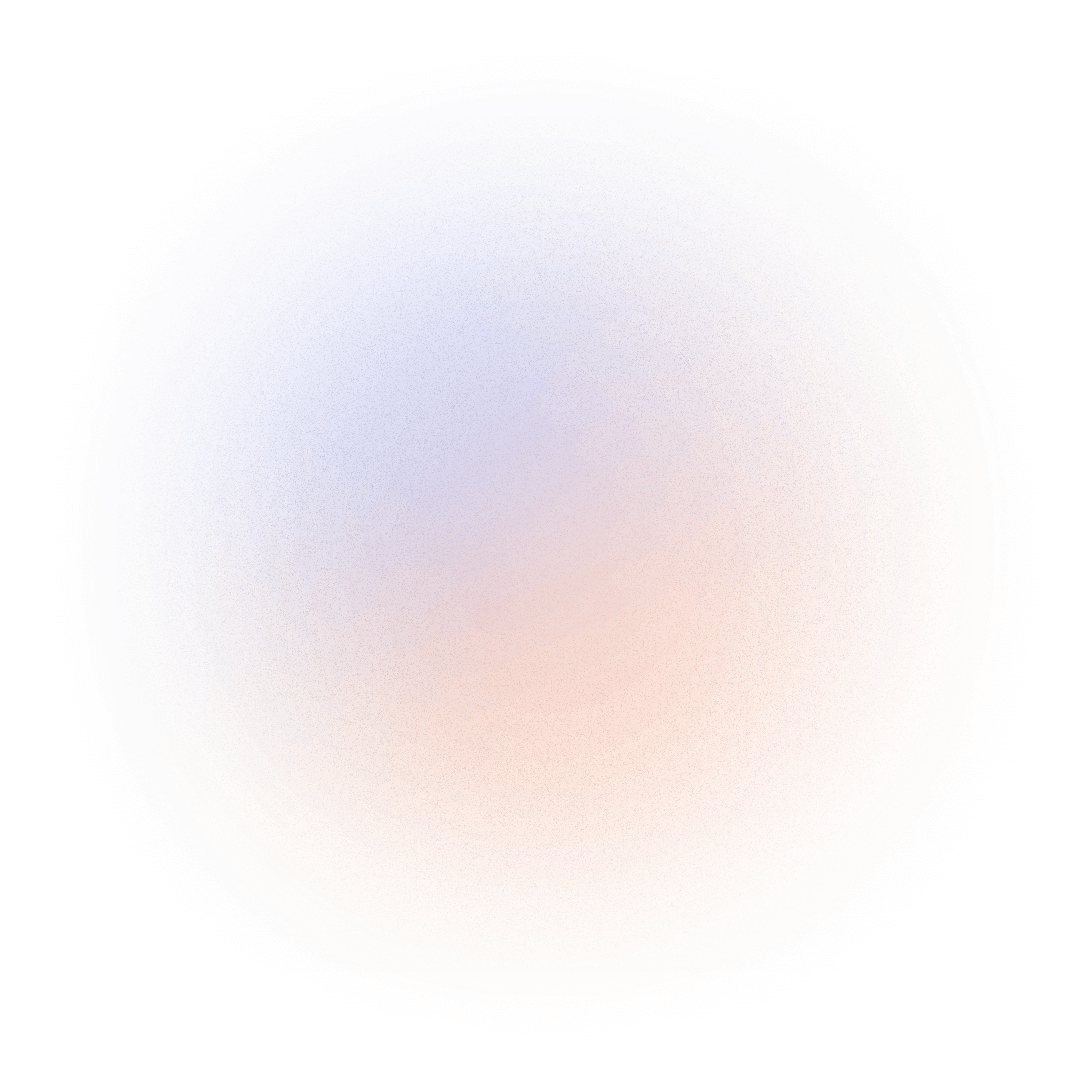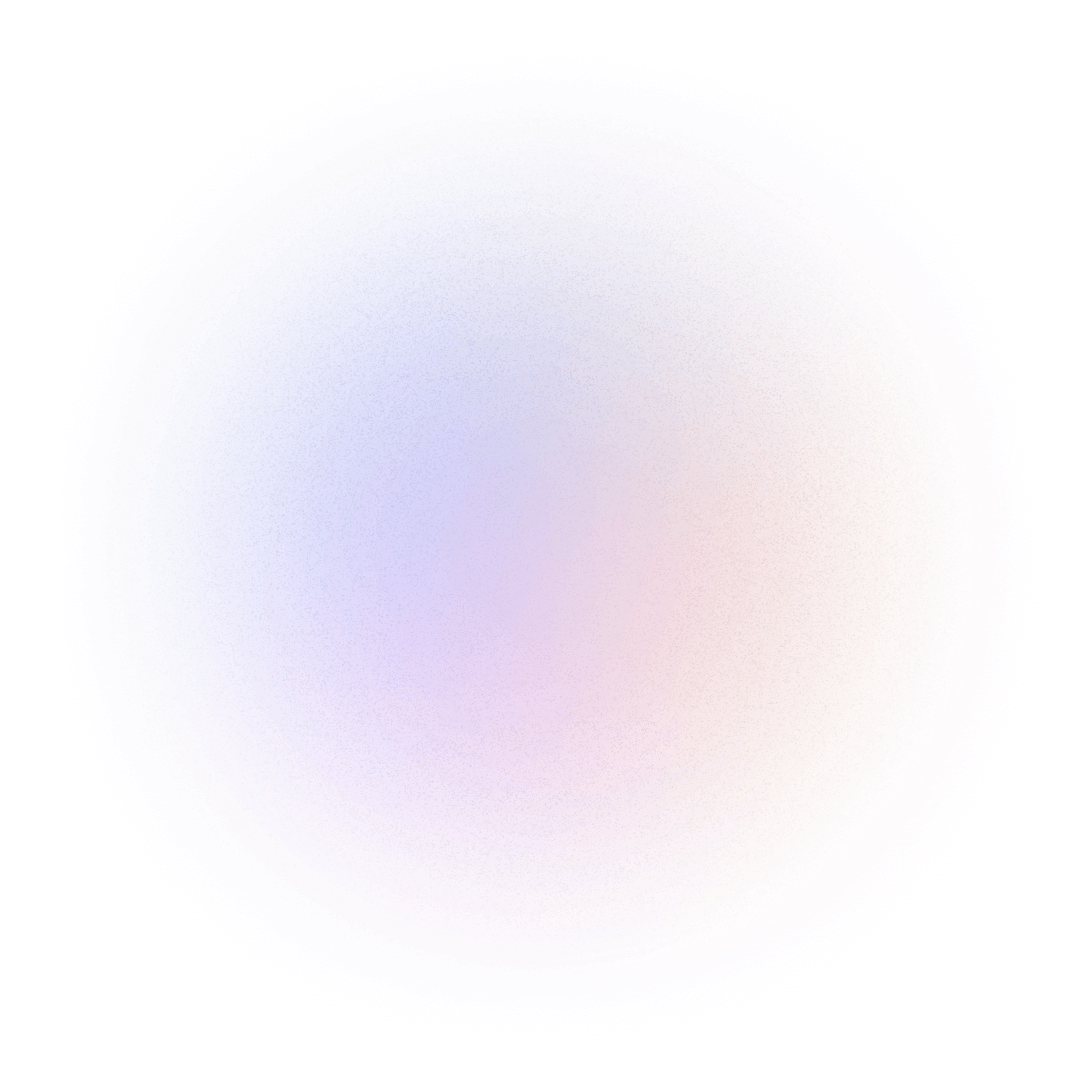|
多收了三五斗之重庆市潼南教师版 XX县教委的办公楼对面的停车场,横七竖八停着乡村里进城来的摩托车、自行车、助力车。车上一般都坐了两个人,把轮胎压得很瘪。教委的大门口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楼梯。教委办公室就在六楼。朝晨的太阳光从铝合金门窗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办公室外面晃动者的那些教书匠上。 那些教书匠大清早从四面八方赶来打听消息,到了教委,气也不透一口,便找到教委领导占卜他们的命运。 “公务员人均17000,教师没有!”领导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啥子?”教书匠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上个月,你们不是说教师有14000么?” “17000块也说过,不要说14000块。” “哪里有变得这样快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小道消息象潮水一般涌来,说不定今后连13个月工资就没了呢” 刚才犹如开F1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国家照应,**政策好,当官也经常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一年有这么14000的津贴,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教书的好,我们回去在家里喂猪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大腹便便的领导冷笑着,“你们不教,就没人教书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毕业生,本科生不够,专科生又有都还有剩的了。” 本科生、专科生,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教已经教了一辈子的书,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教呢?买房欠下的债是要还的,还有子女教育,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到重庆去教吧,”在重庆,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大腹便便的领导又来了一个“嗤”,挥舞着手中的中华烟说道:“不要说重庆,就是广东去也一样。只是,这是政策性的东西,今年的教师没有津贴。” “到重庆去教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重庆要考试、面试,知道他们要我们交多少报名费!就说依他们说的交钱,哪里来的这么多现钱?” “领导,能不能帮教师多少争取一点?”差不多是绝望的声气。 “多少争取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这次工资改革,教师是最大的赢家。我都不好意思去为你们争取,去了肯定要被批评,就是说替你们白挨训,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津贴一点没有也太不对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明明教师法规定教师待遇不得低于公务员,你们教委的人也说过的,教师有14000,我们想,今年总该有一万多块吧。哪里知道一分钱没有涨呢?” “领导,要是有你们所说的14000就心满意足了。” “领导,教书很辛苦,你们行行好心,发点补助吧。” 另一位领导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工资低,不要教书好了。是你们自己要教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教委有的是权,你们不教,大把的人等着教。你们看前不久招聘几十个农村定向教师,几百人报名呢!” 三四个教书匠从楼梯下升上来,教书匠里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教书匠的肩背上。 “听说没有,津贴到底多少钱。” “没戏了,教师一分钱没有!”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啥子?”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然而书还是要教的;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听从教委的管理,因为贫寒的老师还是离不了那一点点可怜的工资。 在教师法是否具有权威辩论之中,在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是否减少的争持之下,结果停车场的车越来越少了;教书匠朋友把自己多年心血献给了XX教育事业,得到的只是重庆市对义务教育的一点补贴。” “领导,什么时候才能领到钱啊?”工资要经过人事局、财政局、教委几道手续才能到教书匠手中,好象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土包子”夹着一枝中华烟的手按在键盘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钱早晚会发给你们!不会少你们一分钱的。补贴发放是要经过一定程序的,你们慢慢等到起!” “那末,只有指望学校发点钱了。”从历年的经验上来看,年终的时候,总有百把块钱的教学奖。 “敢!”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公用经费,你们敢乱用,可是要想挨处分?” 发点钱得挨处分,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想了想今年还有没有余钱过年,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心有不甘地离开了教委大楼。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教委,另一批人又从楼梯口跨上来。同样地,在办公室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今年以来那14000的诱惑所带来的快乐。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教书匠朋友今天进城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生活用品用得差不多了,须得买十包八包回去。各种教辅用书也要带几本。蔬菜、肉类什么的在乡下卖得贵,如果在城里的超市里买就会很划算。陈列在橱窗里的品牌服装听说在打折,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进城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一套,儿子一套,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化妆品。难得今年政策好,工资也听说随着公务员一起上涨,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房款,子女的学费、生活费,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台电脑。这东西实在怪,可以看电视,听说还可以在BBS上发贴,比起电视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教委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该到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飞了腰包。年关将至,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买点年货勉强过年,这要回家与老婆商量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回乡下去未必就会好多少,在城里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欠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名豪广场周围溜达。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领导。女人臂弯里钩着包包,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路边的游戏机、肯得基、玩具店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小车车,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嘟嘟嘟。 好吃好吃好吃,“佳乐士刮刮叫,鸡翅一只8元真公道,老师,带娃二吃一只去吧。” 几家品牌的伙计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老师,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老师的皱西装,他们知道,老师难得逛一回商场,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老师把积攒多日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生活用品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波奇屋的鞋子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在报国商业城随便买双就是了。衣服呢,预备买两套的就买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买的就单买了儿子的。SK-II什么的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小汽车、手枪什么在小孩手里刚玩上,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电脑的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五六千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白发苍苍的老爷子老娘亲就要一阵阵地埋怨:“猪肉这么贵,你们却贪好耍,花了几大千买这些东西来用,今年过年吃什么?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变形金刚。变形金刚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教书匠们还打了一瓶老白干,向卤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广场的长凳上,几个凑着一堆便坐着开始喝酒。小孩在宽阔的广场上打打闹闹,又拣起各种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这个学校的,那个学校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长凳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教师一分钱津贴也没有,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教师工资低,没津贴,今年还是工资低,还是没津贴!” “今年物价涨的太厉害了,去年猪肉只卖几块钱,还能灌几十斤香肠呢。” “我儿子成绩又下降了。唉,教书匠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那么认真教书呢,你这猪脑壳!我们要将孩子培养成才,宁可教学成绩差些,让他们扣奖金!” “也只好这样了,将学生培养成才了,还不是人家的命好,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学生给我们发津贴!” “教书真个寒心!” “辞了职打工去吧。我看打工的倒是满可以的。” “打工去,各种摊派可以赖了,各种培训费、考试费也不交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打工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我看,到深圳去打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深圳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薪水有七八千块。七八千块,相当于几个老师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金融危机之后,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教书,到底替谁教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想起了教委大门口那“富国强县,教育优先”的横幅,就说:“就是替教委教的。 我们吃辛吃苦,摸里贪黑,把学生教了出来,当官的嘴唇皮一动,说‘教师没有’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整没了!” “教委能帮我们争取一下那就好了。凭良心说,一年一万的津贴差不多了,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哈鸡巴,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晓得么?他们教委的是公务员的,他们自己有钱就行了,不肯替教师说话。” “那末,我们的教书的也有尊严,为什么要歧视教师?为什么不按照《教师法》办事?” “我刚才在教委里这么想,关键还是要将自己的孩子教好,让孩子出人头地,自己往后没得饭吃,就去吃孩子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闪烁着一丝幽怨。 “真不把教师当人看,惹毛了,老子们罢课!老子不怕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最近,听说渝北、黔江、秀山、江津、永川、江北教师都在行动!” “教委是早有预防的。” “今天在这里乱说,说不定也会秋后算账的,谁知道!” 牢骚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家。 城市的街头便冷清清地刮着寒风。 第二天又有一批老师或走路或坐车来到教委咨询。城里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最近常常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