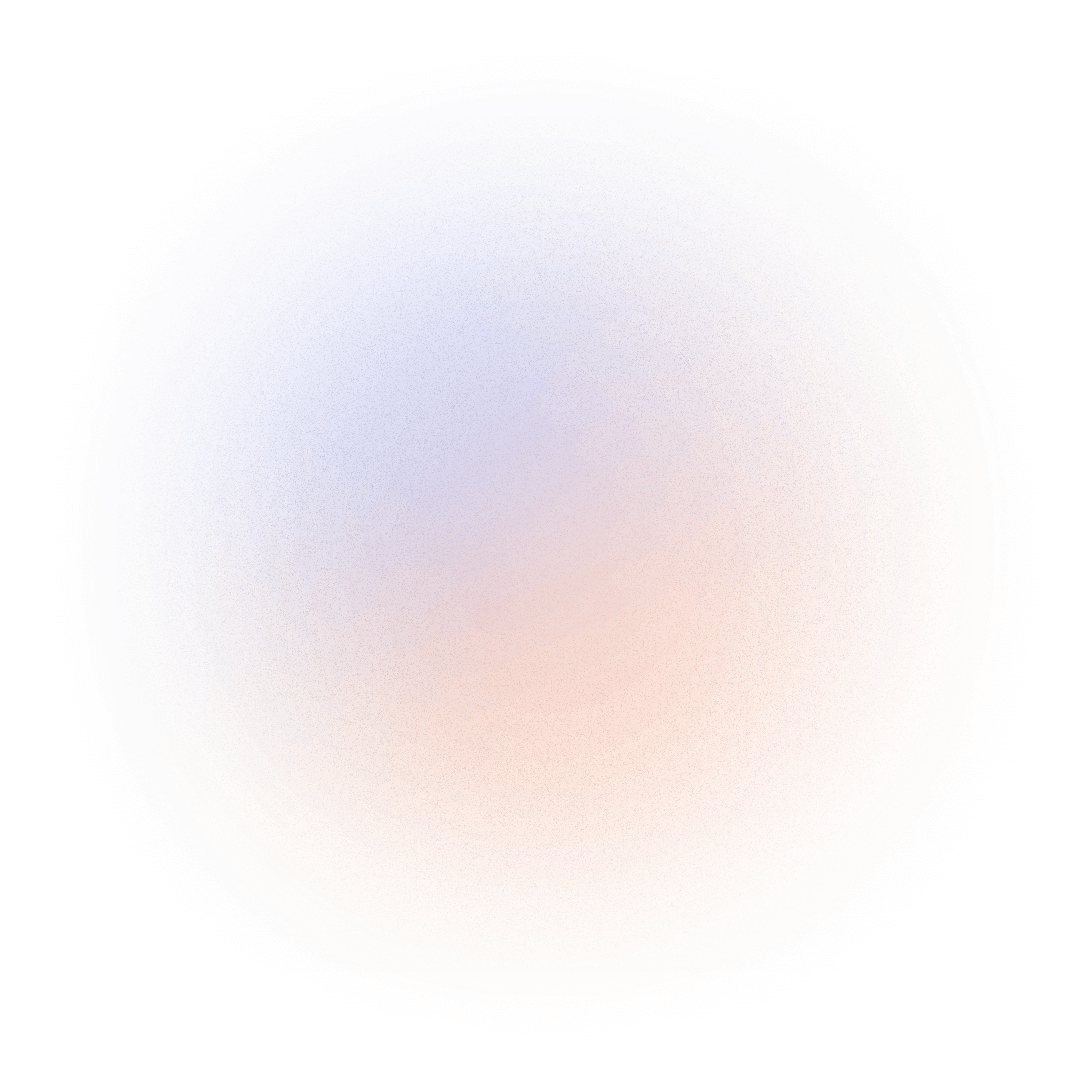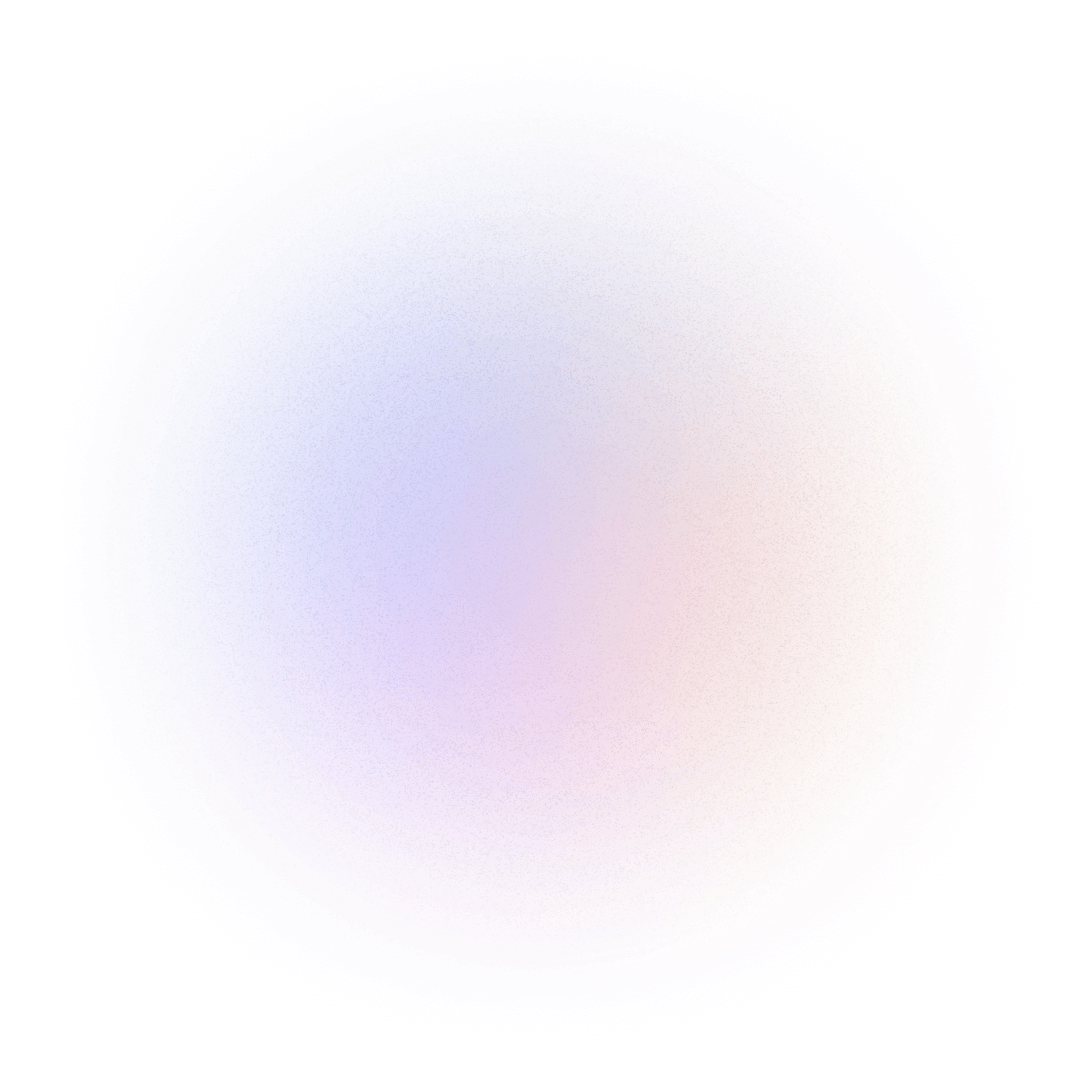我的团长我的团 第二章 TXT下载在线阅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于我们|信息举报|无图浏览|用户申诉|手机版|APP客户端|潼南论坛 ( 渝ICP备14010238号-7 )
GMT+8, 2026-2-14 11:50 , Processed in 0.018883 second(s), 15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5 Discuz! T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