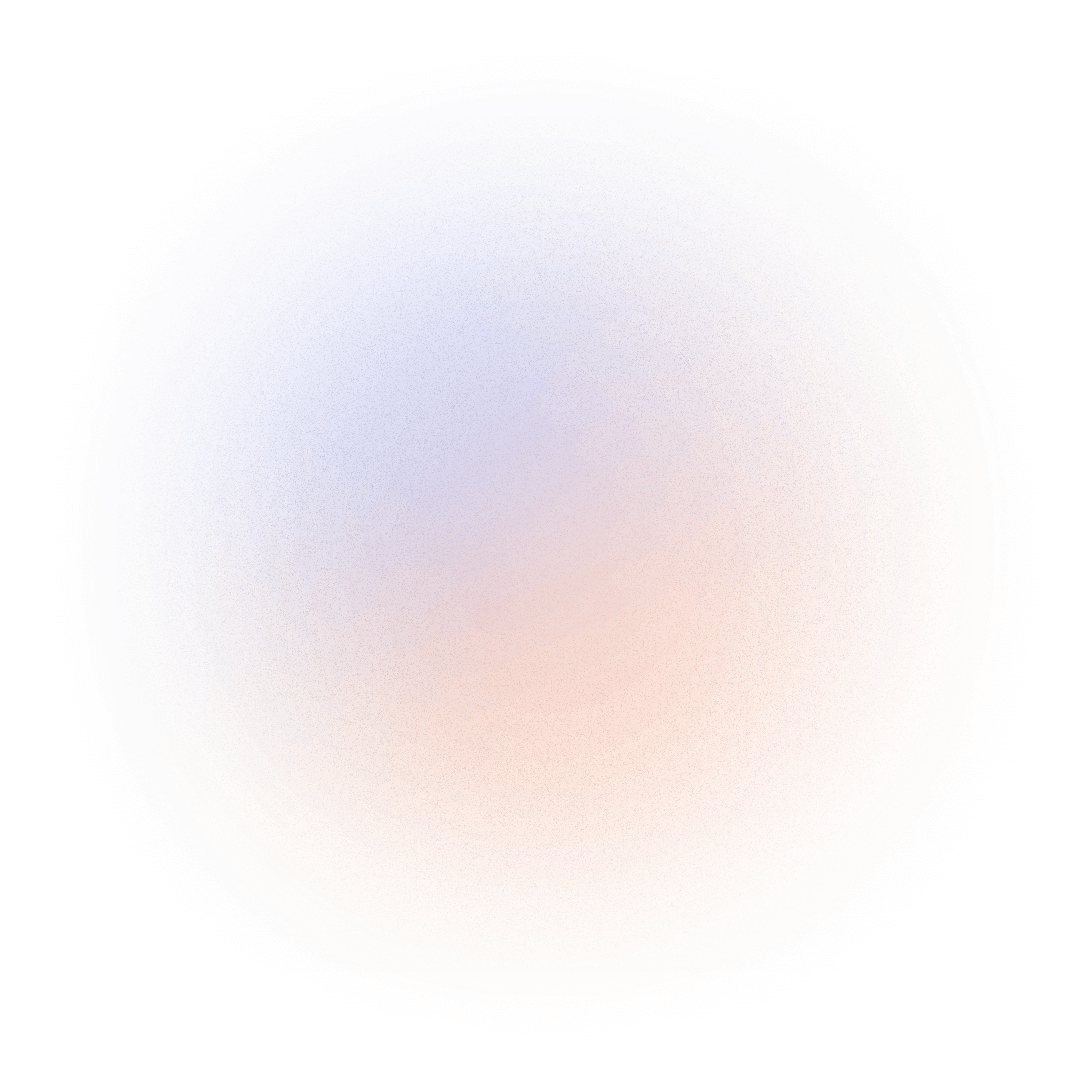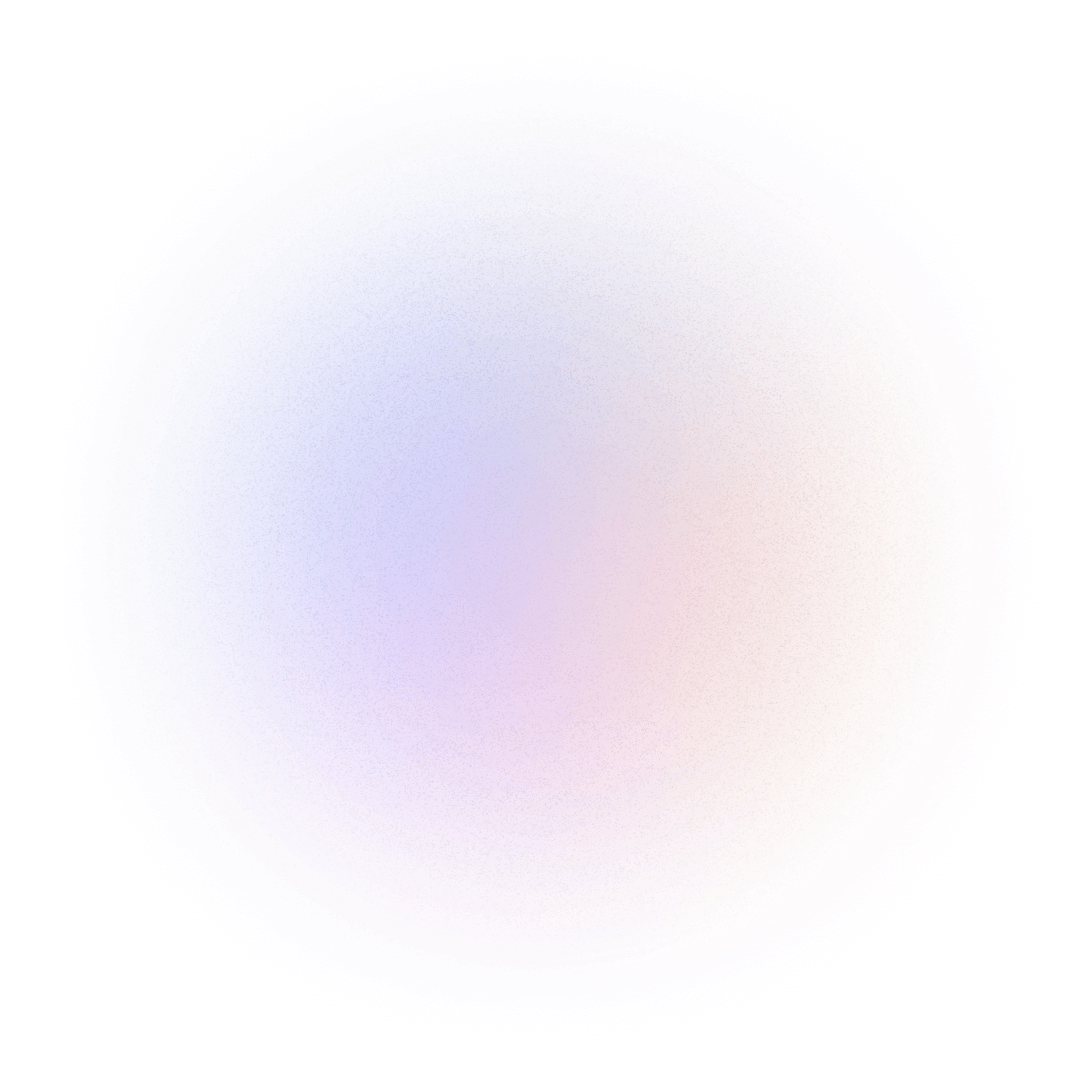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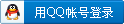
×
印 象 红 苕
红苕,又称红薯 ,或称蕃薯 ,至于为什么有这些称谓,我无法考究,也不想去考究,同一样的东西,就如有《红》学者拈着曹雪芹的长辫子去研究曹雪芹有多少白头发一样毫无趣味。 儿时,从四岁起随母亲回到她的故乡潼南农村生活的十来年里,我最怕见的就是红苕。那时,每餐除了红苕还是红苕,这一顿是红苕汤,下一顿是焖红苕,家里最好不过的就是红苕稀饭。每当我端着盛了红苕稀饭的碗,常常走到土墙茅屋的室外,去比较天上的太阳和我碗中的太阳谁更圆谁更亮,然后拨动碗中多见红苕少见米的饭汤,看太阳在我碗中涟漪里被扯碎又被镶圆的影像,时不时让泪水顺着面颊滴落进碗里,再把镶圆了的太阳砸碎。少不更事的童年,也常抱怨母亲干嘛不在饭里多丢几粒米,每当这时,母亲只会唉声叹气地说,儿子,这是红苕稀饭,不是稀饭红苕,将就点吧。——当然,也有让人期盼的时候,那就是有亲戚过生日,结婚,嫁女抑或老去,每逢那种机会,母亲就会用少得可怜的麦子去换回一把干面或者东寻西找用分币角币凑出一元钱、两元钱作为礼物,带着特别兴奋的我一同去。一到亲戚家,我就会暗暗高兴,盼望早一点上饭桌,学着大人样假装矜持却暗地里使劲狼吞虎咽在风箱土灶里用柴草焐出来难得一见的红苕焖锅干饭和想像得出来的蒜苗炒风肉,还有那用红苕粉和着姜米与炒香风干肉丝用水煮出来,看着就像水晶般晶莹透亮却很难用筷子夹得住的潼南风味滑肉。 那时走亲戚,主人家是断不会给客人盛饭的。一锅焖锅饭,是按大约六七斤红苕一斤米的比例,先把米煮得半生不熟滤出米汤,锅里垫上砍成小块的红苕,再把米饭覆在红苕上用火焖出来的。主人若给客人盛饭,红苕多了得罪客人,米饭多了不够打点。记得有一次到亲戚家,上了饭桌,端上饭碗,自己跑去盛饭,心想一定得多盛米饭少盛红苕,一到锅边抄上锅铲,狠狠一铲下去,心想全要米饭不要红苕,结果锅底全是红苕,想把那抖掉重来,可一看后边还有好几个人端着碗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我面前的锅,我只好把一锅铲红苕全扣进碗里,再在上面铲上点米饭。上得桌来,一桌子人又全都看着我,看我那碗全是米饭没见红苕,那一张张五味杂陈的脸,真让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好好捶自己的胸口扇自己的耳光。鼓起勇气,我再看别人的碗,别人的碗里却只见红苕不见米饭,慢慢地再仔细一观察,那些人非常聪明就只在米饭上盖了为数不多刚好遮住米饭的一点儿红苕,吃的时候再用菜把米饭遮住。我三两下把难以下咽的红苕鼓起勇气塞进肚里后,再去锅边一看,锅里没了米饭只有红苕。端着空碗,心中的郁闷,心中的失望,心中的那个无比凄凉,此时此刻只有我自己知道。盛了几许红苕回到桌边,桌上稍有点油星的菜也早已被荡涤一空。母亲从她的碗里扒给我两小砣滑肉,我慢慢咀嚼着,想从里面寻找出久违了的猪肉的滋味,可里面却一点儿肉末也没能见到。我看看母亲,母亲也看着我,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了哀怨,读出了忧伤,更读出了对生活的无奈。一顿饭下来,母亲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用黄草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炒风肉递给我,再三叮嘱不要让人看见。我把肉如珍宝般捧在手里,眼泪却再也忍不住一直往下流………… 时过境迁,儿时对红苕的深恶痛绝虽在记忆里已经打上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可现在对红苕的感觉却又另是一番情愫。现在品尝红苕,虽也每每让我想起儿时的情景,想起我的母亲,可此红苕却非彼红苕,先前的红苕是为了生存,现在的红苕却是为了养生。所以,隔三差五,我会让家人买点红苕,变着花样做成各种不同味道的食品让一家人在餐桌上去你争我抢,用以清扫让油腻长期侵占着的肚肠。如果时间长了,没吃上一点儿红苕,反倒让人觉得周身或多或少地不舒爽。——红苕,一个可悲又可喜的名词;红苕,一种可恨又可爱的食物,印证过历史的悲哀,更见证着现在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