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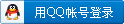
x
本帖最后由 灯火阑姗 于 2014-9-1 11:11 编辑
家在水巷
文/宁顺蓉
昨天吃过晚饭后,闲闲地逛着,不知不觉就到了曾经我住过的老街,水巷子。这里已经和记忆中的水巷子大不同。顿时生了真是时光易逝,物事人非之感。
水巷子的半边街,也就是曾经的商贸公司,有点年龄的人都会记得这里曾经是一个门市,里面卖过包子馒头,又经营过日用百货的。后来卖给一个经营玻璃生意的袁姓商人,第二家周家,再就是彭家,杨家,袁家。袁家后来搬走后,就住着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这里住。她唯一的儿子是个残疾人,至今身体都只有七岁儿童的身高。这排平房就齐这里有一个不宽的巷道,也就是在水巷子约三分之二的长度吧,住着刘姨的家,刘姨家的后面住着李家,谭家,赵家。
再就是我家那排平房是和这两排平房呈直角,横起的。就住在李家的对面了。我们这里称为“都是对门时户”的。而和我们比邻而居的就是:第一家是调味业,属于饮服公司的,是做豆腐和豆腐干,酱油和醋。记得在调味业里做事的一个中年妇女,名字记不起了,但我听别人把她喊“罗喳弯”,她平时说话的声音的确是挺大的,只要一激动声音就更大啦。第二家还是调味业的。第三家是胥家,第四家是江家,接着是解放前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医生的李医生家,过来就是我家了。平房也就止于我家的旁边。再过去就是房管所的办公楼,宿舍和公共厕所了。
印象深刻的就是在调味业的第二间房子的门口,有一个碓窝。是用来碓石膏的。每天早上天刚刚亮就听到两个人拿着石椎子往碓窝里的石膏砸去而发出沉闷的“砰砰”声。我们小孩子有时吃饭,把菜刨到碗里头就跑到这个碓窝上面蹲起,边吃饭边看风景。
这些曾经的平房,曾经的吊脚楼仿佛一夜之间都烟消云散了,都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建筑院墙和待建筑的建筑脚手架在里面存放着了。
而仅有的,还有现在过路人眼中的只有剩下来的半边了,也就是从河街进巷口的左手边:第一家曾经是一个食店,后来成了一个理发店和茶馆了。然后是黄家,宋家,彭家,袁家,李家。彭家后来从发财以后,把房屋转租给了一直开着一个小诊所的医院至今,平房的尽头是李家。
再就是两层楼房的房管所了,穿过房管所宽宽的大门和巷道,里面有一个较宽的坝子。在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的早中期,这里曾经是我们小孩子玩耍的天堂。房管所的房子就住着约三、四家人和存放单位的物品,后来把办公的地方转给了饮服公司。从这里起到河坝都是荒起的,是泥土和鹅卵石,上边不时应季地冒出一些不知道名称的小草和小树,记得那时的人们把家里的垃圾都会倒在这里,这里成了一个不知名的垃圾场所。因为是从这里下河取水等等,渐渐地也就形成了一条小路,我们小时洗衣服都主要是从这条最近的路下河坝去洗衣浣裳的。后来,家家户户安了水管后,这条路又成为我们小孩下河洗澡,大人休闲的必经之路了。
后来在八十年代末期,在这个临时垃圾场上面修起了一座高楼,成了综贸公司宿舍楼,但现在这座高楼早已经不在了。
水巷子位于河街的中间,也是以水巷子为界,河街分为了上河街和下河街,统称为上街和下街。和河街呈丁字形。
人们的意识里面,巷是比街道窄一些的一条供人们通行的道路,可是水巷子的巷道并不比河街的街道窄。它是河坪村人路过的重要路径。房屋都是黑瓦白墙的平房,俗称为“穿架房”。有时一阵风吹过屋,风透过有缝的黑瓦,让人激伶伶地感到一阵凉意,风卷着灰尘也都吹到屋里了。这就是叫“过堂风”,平房高到可以在里面隔上一层做个小阁楼。
里面的风景就不敢恭维了,因为长久地烟熏火燎都是黑黑的,只能在过年之前,有的人家拼一些报纸贴在黑黑的墙上,屋子里面才会显得亮堂一些。爱好的也会找些石灰兑上水,抹在墙上这样的白又能管很长的时间了。
时光进入了八十年代中期,有条件的家庭把以前的老屋拆了,修建起了两层或更高的楼房居住。
从有记忆以来,我就在这条街上长大的,在水巷子的最深处,和仁河水比邻而居着。每天晚上我们伴随着河水的欢唱声而进入梦乡。听家里人说, 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春天,大舅找了一颗一人高的小杨槐树栽在了我家的吊脚楼后。我一天天地长大,小树也渐渐地长成了大树。直到我读初中那一年,有人从我们家吊脚楼的后面取沙,把沙给全挖起走了,大树也就悬空起。没多久,遇上了几十年难遇的洪水,把大树给连根拨起,眼看着大树在波涛浪滚的洪水面前挣扎,发出痛苦的声音,然后累倒了慢慢地倾斜。记得那时我正放学在家,看着大树一点点地倒下发出“齐齐查查”的声音,我也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连着那几天心里都为之而感伤,因为它陪伴着我度过了我的童年,正陪我走着青春年华,可就这么地被人为地伤害着,能不让我伤怀吗?因为这颗树,我写了几篇作文,写着它的历史,写着它的四季变化,写着我们对它的情感寄托。
后来,国家在这后面修起了河堤,阻挡住汹涌的河水的浸蚀和漫延。同时,在我家吊脚楼的后面也起了一排河堤至预置板厂的那个河湾。
水巷子的尽头,也就是在刘姨家的对面有一个宽宽的坝子。记得以前大概是七十年代初吧,还是一片空地,下雨天里面不时就塘着水,有的家里养的小鸡,鸭子和鹅都爱在里面玩耍,我们小孩子就拿着小木棍在里面逗这些小动物们。把它们逗得“吱吱嘎嘎”直叫,直到大人们听到声音把我们撵起跑……
后来,不知道哪天起在这里修建了一个花园,呈扇形,起了半人高的花台。刘姨就把里面给打扫出来,在里面栽上了牵牛花,芭蕉树和火炮树等。到了夏天,里面的花争相开放,小树也渐渐长高了长壮了,很是热闹。记得刘姨栽的芭蕉树,在小小的我的眼里它长得好高大。那时六,七岁的我有个小小的想法,“蕉”和“花椒”的“椒”不是同音吗,可我又不认识字,就以为这两种植物是同一类的。花椒有籽,那芭蕉的籽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缠绕我好多天了,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有一天我刚好路过,就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啦。我很快地爬上花台,那时小小的我又没有芭蕉树高,就够起手把芭蕉树给掰弯了下来再看里面的根部有没有籽籽。可我没看见啦。还正看呢,感觉到自己的背部被什么敲打了一下,同时后面发出一阵暴喝:“你在做啥子?!”我回头一看,是刘姨家的儿子一张气愤的脸:“你把芭蕉树掰烂了!”我吓得赶紧跳下花台,脚一下子给崴了,可我都没顾上疼,一下花台就一溜烟地跑了。直到跑了很远才停下奔跑的脚步。
到了吃中午饭的时间,我们正吃着饭。就听到刘姨心疼得发出叫声:“天哪,我的芭蕉树遭哪个背时的给我整烂了哦!”刘姨的大嗓门声多远都听得见。我的心咚咚地跳着,就听到刘姨的儿子咕哝了一句。后来就没听到声儿了。
那几天,只要是从那里经过,我都不敢看那耷拉着脑袋的芭蕉树,直到好久远远地看到刘姨的儿子,我都会绕道不从他身边过路。
时光,似乎还停留在以前,还停留在儿童时代和青葱的岁月里面……
那时的我正走在有梦想的青春年华,而当我现在在回忆这段时光时,却发现自己的头发上已有几多的白发正在陪着我走过时光的隧道……
这是一段难忘记的时光和岁月,它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曾经的,现在的水巷子人的脑海深处清清楚楚。
水巷也是我童年的记忆和梦,是我的梦里水乡。不知道过了多年以后,梦里的水巷在我的脑海里还会残存好多的记忆!
伴着水巷的记忆我们正在青丝变成白发,可水巷之情却永远地留在我们那一辈,和我们的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陪着我们老去,远去。取而代之不再是小巷的名称,不再是上河街和下河街的名,而会被某某花园某某小区所代替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此而发出感慨和泪流满面。
|
|